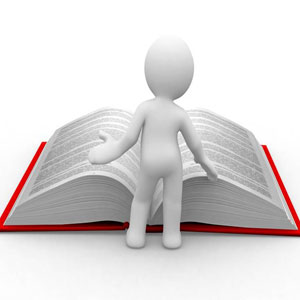内容
一、哈特对于奥斯丁“法律命令”理论的批判
什么是法律?关于这一问题各个法理学家在自己的著作中展开了永无止境的争论。19世纪的法理学家、分析法学的奠基者奥斯丁在其代表作《法理学的范围》一书中对这一疑问给出了肯定性的回答: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或者说是政治优势者对政治劣势者设定的规则。奥斯丁的法律命令理论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即命令理论和主权者理论。所谓命令理论是指当你表达或宣布一个愿望,即将让对方做或容忍一些行为,如果对方不服从将施加惩罚,那么这一愿望就是命令。一个命令区别于其他意义的愿望在于其背后的强制力。主权者具有如下的特点或显著标志:其一,特定社会中的群体,处于一种习惯服从或隶属于一个特定或一般的优势者的状态。而这样一种一般的优势者,是某个特定的个人,或者是由若干个人组成的某个群体或集合体;其二,被习惯服从或隶属的某个个人,或者由个人组成的群体,并没有处于一种习惯服从其他特定社会优势者的状态。
但奥斯丁的法律命令理论未能成功地呈现某些法体系的明显特征。首先,“法律命令说”把“被强迫”等同于“有义务”,此种缺陷在“抢匪情境”下充分展示出来。A命令B交出他的钱,并且威胁他说,如果不遵从的话,就要射杀他。如果B服从的话,他就是“被强迫”交出钱的,但这并不意味着B“有义务”交出钱。“被强迫”往往与当事人的主观信念和动机相关,通常情况下说某人被强迫去做某事,意味着他实际上做了这件事。不同的是,说某人“有义务”或“负担义务”是隐含着规则的存在。人们对规则背后之社会压力的重要性或严重性的坚持,是这些规则是否产生义务的主要因素。其次,我们观察各个法律的特征会发现,只有刑法能够具备此种法律命令的属性,有许多其他种类的法律,尤其是那些授予法律上权力的法律,即裁判或立法的权力(公共权力),或者创设或改变法律关系的权力(私人权力),这些法律无法被解释为强制性命令。最后,关于“习惯性服从”,奥斯丁认为,民众对命令的“习惯性服从”源自制裁因素的不断延展,但这却无法说明,一旦法律所维系的主权者发生更迭,则在新的习惯形成之前,依据奥斯丁的学说,却会出现法律事实存在却不能被判定为法律的情况。
二、哈特眼中法律的构成要素
哈特认为这个理论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其所由建构的要素,即命令、服从、习惯和威胁等观念,并不包括,或者说不能通过把这些要素组合起来产生“规则”的观念。若要周延地处理法体系的复杂性,就需要去区分两种相关但不同类型的规则。在其中一种规则的规范下(这种规则可以被认为是基本的或初级的类型),无论是否愿意,人们都被要求去做或不做某些行为。另一种规则则是依附在第一种类型的规则之上,或者说,对第一种类型的规则而言是次级的(secondary);因为它引入了新的、取消或修改旧的初级类型的规则,或者以各式各样的方式确定它们的作用范围,或控制它们的运作。第一种类型的规则科以义务;第二种类型的规则授予权力,包括公共的或私人的。第一种类型的规则规范的对象是人们具体的行为或变动;第二种类型的规则的运作方式不只是导致了具体行为或变动的规则,也产生了责任或义务的创设或改变的规定。真正的“法律科学之关键”就是这两种规则的组合,如果能够理解这两种类型的规则以及两者间之相互作用的话,我们就能厘清“法律”的大部分特征。
如果某个社会的生活只依靠初级规则来维持,则这个社会必须满足某些条件,其建立在一些关于人性以及我们所生活之世界的自明之理之上。第一个条件是,这些规则必须以某种形式对滥用暴力、偷窃,以及欺骗等进行限制。第二个条件是,假如由体力近乎平等的人如此松散地组织起来的社会要维持下去的话,则在接受规则的人和拒绝规则(只有对社会压力的恐惧才会使他们遵从规则)的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后者只能是少数。
但是这种社会结构存在着明显的缺陷。第一个缺陷是初级规则的不确定性。这种群体生活所依赖的规则并不会形成一个体系,而只会是一批个别独立的标准,没有任何可供鉴别的或共同的标识。第二个缺陷是初级规则的静态性格。此种社会所知的唯一的规则变动模式将会是一种缓慢的生长过程。在这样的社会中,无论是取消旧规则或引进新规则,不存在任何变更规则的方法。因为,这样做的可能性再次预设了一种不同于“科予义务之初级规则”的规则之存在,然而,在此社会中却只有初级规则。简单形式之社会生活的第三个缺陷是,用以维持规则的社会压力是分散的,因而是无效率的。如果没有一个机构,被授权能够终局地和权威地确定违规事实,那么人们总是会为一个公认的规则是否已被违反而发生争议,且这个争议将不确定地继续着。
最简单之社会结构的三个主要缺陷,其每一个的补救方法都是以属于另外一种类型的规则——次级规则来补充科予义务的初级规则。对每一个缺陷之补救方法的引进,本身就可以被当成由前法律世界迈入法律世界的一步,因为每一个补救方法都引入许多遍布于法律中的要素,而这三个补救方法结合在一起就足以使初级规则的体制转变为法律体系。
对于初级规则体制的不确定性最简单的补救方式,就是引进“承认规则”(a rule of recognition)。承认规则会指出某个或某些特征,如果一个规则具有这个或这些特征,众人就会决定把这些特征当作正面指示,确认此规则是该群体的规则,而应由该社会的压力加以支持。此规则意味着一个鉴别科予义务之初级规则的决定性规则。对于初级规则体制之静态特质,我们将引进所谓的“变更规则”(rules of change)来加以补救。此种规则最简单的形式就是,授权给某个人或一些人,为整个群体的生活或其中某一阶层的人的生活引进新的初级行为规则,以及废止旧的规则。对于因社会压力之分散而导致的无效率,我们所要做的第三个补充是裁判规则,这一种次级规则授权给某些人对于在特定的场合中,做出初级规则是否被违反的权威性决定。裁判规则提供了体系中集中化的官方“制裁”。
至此,我们不但拥有了法体系的核心,而且在法学家和政治理论家们之间的许多困惑现象的分析上,也有了最强而有力的工具。但是,我们必须明确:虽然初级规则和次级规则的结合,说明了法律的许多面向,而值得被我们赋予中心的地位,但是这个结合本身不能阐明每一个问题,初级规则和次级规则的结合处于法体系的中心,但它不是全部。
三、两种法律层面的观察视角——内部面向与外部面向
哈特在语词的分析方面采取了“内在面向”与“外在面向”的方法,既存在置身于语境内部对语词含义的观察和分析,又需要跳出具体语境,从外部视角看待相关语词在法律体系当中的具体含义,从而寻找最符合实际需要的语词概念及其用法。外在面向是内在面向的前提。针对规则,人们可以站在观察者的角度,本身并不接受规则,或者人们可以站在群体成员的角度,而接受并使用这些规则作为行为的指引。我们可以将二者分别称为“外在”面向和“内在”面向。
外部面向是指规则实践的外在观察者所持有的视角,他们会观察某种规则在实践中会导致何种结果,并据此判断是否遵守规则。法律的内在面向则意味着站在群体成员的角度,接受并使用这些规则作为行为的指引。也就是说,个体是以规则实践的参与者为视角,接受群体生活的准则,并将规则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这也就意味着,当其他人的行为偏离行为规则时,个体依据规则对他们进行批评并要求他们遵守规则的态度;当人们在遇到这种批评和遵守的要求时,他们承认这些要求具有正当性。比如在十字路口选择是否闯红灯:持内在面向的人不闯红灯,是因为其承认规则本身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持外在面向的人选择不闯红灯的原因是惧怕受到处罚。换言之,若能成功逃避处罚,他们就不会遵守相关的交通法规。
持内部观点的人在鉴别特定规则时,最普通的表达语句是“法律规定如何”。他们对于承认规则不加说明而直接适用,是因为他们对于承认规则持一种普遍认同且共同接受的态度。持外部观点的人,一般使用的语言不会是“法律规定如何”,而是“在英国他们认为凡是女王议会所通过的就是法律”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外部陈述”是一个法体系外的观察者自然而然会使用的语言,这位观察者并不接受规则,而仅仅说出他人接受规则的事实。我们在单纯使用承认规则鉴别某一具体“法律”时,所持的是一种毋庸置疑的、达成共识的、共同接受者的态度;那么据此做出的陈述也应是一种“内部陈述”,因为陈述者不仅认同规则,而且愿意受规则的约束。
四、法律体系的基石——承认规则
哈特没有将道德粗暴地排除在法律规则之外,将法律规则的存在直接等同于法律规则的有效,也没有将法律规则的效力溯及到法律规则之外的“基本规范”中,他将法律规则的有效性界定在法律规则体系内部,需要承认规则解决法律规则的效力授权问题。
承认规则是用来消除法律的不确定性的一种次级规则。该种规则指明了哪个法律规则适用于特定个案的标准和依据。所谓“承认规则”,按照哈特的说法,“会指出某个或某些特征,如果一个规则具有这个或这些特征,众人就会决定性地把这些特征当作正面指示,确认此规则是该群体的规则,而应由该社会的压力加以支持。”承认规则确认其他的规则,但自身不需要被确认。其具有以下特征:其一,承认规则是该法律效力体系效力的终极规则。法律体系内的其他标准或规则的效力最终来源于承认规则,但承认规则的效力不可能来源于其他标准。其二,承认规则是判定法律效力的最高标准。承认规则对于法律效力的鉴别具有终极性。
承认规则并不强调法效力或法实效的问题。所谓效力或实效,一般是从外在视角所观察判断,而生活在某个具体语境下的社会成员并不会询问,他们服从某一法律规则的理由是因为它们存在“效力”,因为一旦他们做出此种询问,那么法律就会跟强制服从的命令毫无二致。是故哈特指出,承认规则的“效力”是规则使用者在鉴别法律的活动中因不自觉地援引相关承认规则而体现出来的;换言之,承认规则不存在“是否有效”的问题;如果必须认为其具有“效力”,也是因为它实际存在,而且为“因为妥当而被采用”。承认规则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在实践中承认规则是一种“官民一致”的判准和社会事实,而不是它是否具备法律效力。
承认规则的存在及其内容是一个社会事实问题:承认规则作为一项社会规则,必须满足社会规则存在的必要条件,即承认规则的存在只与该法律体系的官员有关;个别的法律通过承认规则确定其效力。通过这种方式,个别的法律得以组成一个法律体系。如果有官员接受承认规则,则存在一个有效的法律体系。也就是说,承认规则的存在,必须以法官、政府官员或一般人民适用其所含判准鉴别法律这一实践活动为基础,而实践活动本身即为客观存在的事实。因此,承认规则的存在应视为事实问题。承认规则自身的效力是确定的,承认规则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其效力不取决于其他更高位阶规则的认定与支持,更不需要同一体系内其他规则的认可。
在《法律的概念》的“后记”中,哈特明确地表示:“承认规则事实上就是一种司法上的习惯规则,只有在法院加以接受并加以实践,用以鉴别法律和适用法律时,它才能够存在。它可以被进一步地分解为以下两层意思:第一,“承认规则”是一种行之而成的“习惯”(或曰“事实”),它的存在有赖于法律官员对于“初级规则”之系谱或原则(而非“初级规则”本身)的持续性的反思和接受;尤其是当“承认规则”本身存在不确定性时,仍然“可以由法院来解决”,“在此,运用权力因为成功而事后地获得权威”。第二,过去行之而成的“惯习”对未来法律官员的实践都将构成一种有约束力的“规则”(或曰“法律”)。
五、结论